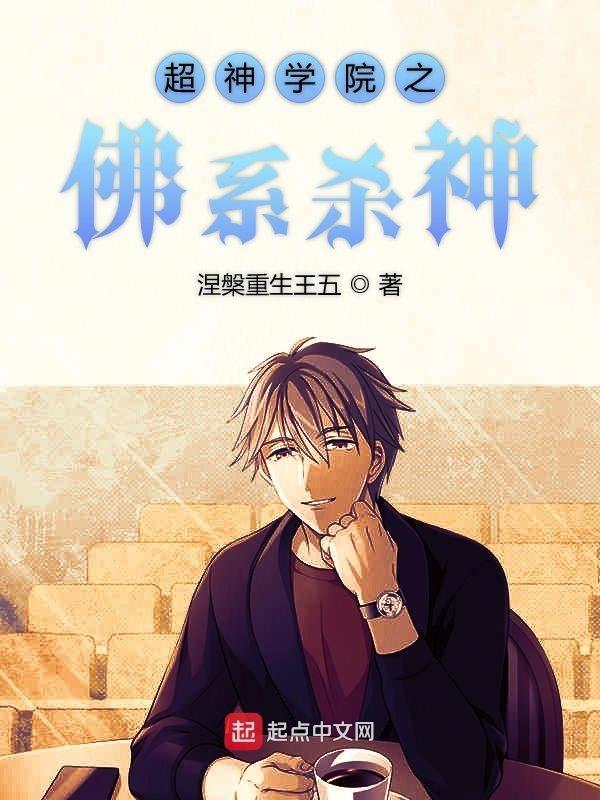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部第九章(第2页)
她告诉别人说有很多人淌眼泪一直淌到硬胡子里,其实根本没有掉眼泪。
但是如果她说看见了,而这件事又使她高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已经快到下葬的日子了。
金属棺材已经严严紧紧地钉合起来,上面盖着花,蜡烛架上的蜡烛点着,屋子里挤满了人,普灵斯亥姆牧师神色庄严地站在棺材前面,一群当地和外地的送葬人围在他四周。
他把自己一颗富有表情的头摆在宽大的皱领上,就好像摆在一个盘子上一样。
一个端肩膀的打杂的人一个类似仆人和司仪之间的精明伶俐的家伙担负着指挥仪式进行的职责。
他手里拿着大礼帽脚步轻快地从大楼梯上跑到下面门道里。
这里挤满了穿着制服的税吏和穿着工作服、半长的裤子、戴着礼帽的粮栈般运夫。
他压着嗓子用刺耳的沙沙的声音对大家说:
“房间里已经挤不进去了,可是游廊上还有点地方”
当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普灵斯亥姆牧师开始讲话了,他的抑扬顿挫的美妙而宏亮的声音把整所房子填满。
当他在楼上基督雕像旁边,时而在胸前绞着手,时而又把手平伸出去祝福时,在楼外面,在冬日的灰白的天空下,房子前面已经有一辆四匹马驾着的灵车在等候了。
灵车后面别的马车排成一长列,迤迤逦逦地一直伸到特拉夫河边上。
大门对面站着两排兵,枪托倚在脚前,站在队伍前面的是封特洛塔少尉。
封特洛塔少尉手里拿出指挥刀,一双热情的眸子注视着楼上的窗户附近几所房子的窗户后面和这一带人行道上都有人伸着脖子看。
最后,前厅里人们蠕动起来,少尉一声令下,兵士们刮剌剌一声响,举起枪来,封特洛塔先生把指挥刀落下来。
由四个穿黑袍子戴三角帽的人抬着棺材出来了,棺材慢慢地移出大门来,向河边等候的马车走去。
一阵风刮来,把香气吹到看热闹的人的鼻子里,吹乱了灵车顶上的黑羽毛,吹动了马的鬃毛,还有车夫和马夫帽子上罩着的黑纱。
全身罩着黑布的驾灵车的马,只留出两只眼睛在外面,不安地转动着。
当四个一身黑的马夫牵着它们慢慢地走动起来以后,那一队士兵便排在灵车后面。
其余的马车按照顺序跟在后面前进。
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跟牧师坐的是第一辆。
后面的一辆是小约翰和一个从汉堡来的吃得满面红光的亲戚。
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送葬行列拖得很长,非常缓慢地移动着,呈现出一副悲凉、严肃的气氛。
每家住户的门前都悬着半旗,旗子一任风儿摆动公司里的职员和搬运夫步行,走在行列最后面。
当送葬者穿过城门,走完通向墓地的一段路,走过一些十字架、石像、几座小礼拜堂和一些叶子落光的垂杨柳以后,就走进布登勃洛克家的祖茔了。
这时仪仗队已经排好,举枪致敬,同时低沉的哀乐也从一丛矮树后面传了出来。
雕刻着家族纹章的大石碑又一次被搬到一边,在一块光秃秃的矮林旁的墓穴四周,送葬的绅士围成一圈,只是这次要下到墓穴里和祖先们葬在一起的是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罢了。
这些人都是有地位、有财产的人,有些人是议员,这从他们的白手套和白领带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站在那里,或者低着头,或者悲哀地看着别处。
职员、搬运夫、店伙和粮栈工人聚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普灵斯亥姆牧师在音乐停止后开始讲话。
当他的祝福词在冷空气里结束以后,大家都走过来,准备和死者的兄弟和儿子再握一次手。
这一队人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带着一副一半心不在焉、一半迷惑困窘的脸色,迎接众人的吊唁,他在庄严的时候总是这副样子。
小约翰站在他旁边,皱着眉毛,低着头,避着寒风。
他穿的是一件带金色结子的宽大的水手式的短外衣。
他的一双罩着青圈的眼睛一直俯视着地下,不把目光投向任何人。
- 开局签到送封号斗罗南方乞丐
- 我就是富二代!一块硬板床
- 无尽债务伯洛戈Andlao
- 东京电子游戏大亨小鸡啄小米
- 岳不群也要模拟人生8月12
- 君临法兰西孤山钓雪
- 全职之职业欧皇闪光哈士奇
- 我能修改人设词条堪梦01
- 一万个我纵横诸天正经沧月
- 从成为妖怪之主开始咸鱼配饭
- 神父马维柯学的菜头
- 修仙从熟练度面板开始无人能比的卡比
- 斗罗之我编造了未来视频符何君
- 诡异星巫白银黑铁
- 我的手机能挖矿卖艺小青年
- 我在古代当名师三羊泰来
- 诸天大明联盟饿祸
- 从武侠世界开始种道古今兮
- 黑龙国度不死长河
- 影帝他不想当太监江公子阿宝
- 大明:我,朱棣第四子星月长江
- 人在龙族,刚成魔法少女一叶封妖
- 足坛第一狂徒真狼魂
- 剑本是魔惰堕
- 从天才开始无敌于斗破a小白b
- 傲娇女神爱上我叫我红烧肉
- 见鬼曲小蛐
- 鱼目珠子崽崽猎手
- 病态痴迷(校园青梅竹马H)巧克熊
- 万人迷[穿书]风雪添酒
- 老赵老赵孙潇潇
- 音符瀑布
- 霸总雇我对付他命定的小白花女主启夫微安
- 没你就不行之新征途林木儿
- 孟大小姐惘若
- 四合院之闫家老大星际旅客
- 女儿拔掉了我氧气管东方燿
- 30条短视频助星球避开天灾睡觉能人
- 软腰河豚没有毒
- 欲望娃娃蜜丸
- 地窟逃生百倍奖励[无限流]尝寒
- 炙野八宝粥粥
- 末世被丧尸圈养(强制 nph)xoxoxo12
- 高武:开局觉醒武神系统一夜暴富啊啊啊
- 继父(,甜宠h)四重奏
- 宠头到尾(青梅竹马h)石矶娘娘
- 香江第一长嫂[八零]浣若君
- 龙魂特种兵东方小少
- 长央红刺北
- 文城余华 ="y">巧克熊
- 我的半岛2007懵懂的猪
- 至道孤独小刀书生
- 逃荒被弃,我进深山吃喝不愁江久久鸭
- 五个京圈大佬沦陷后,我跑路了祈天狐
- 狂龙医仙在都市雁门关外
- 空姐背后雪豹
- 一人:我的身上纹满了十凶图爱吃红豆糖水
- 战争宫廷和膝枕,奥地利的天命七年之期
- 三国:我真的只想找死啊一时疏忽
- 摆烂女王称霸娱乐圈南宫琉生
- 华娱:从囚徒到影帝嗷世巅锋
- 苟道修仙:我变成了修真界第一人惊惧一刹
- 娘娘福星高照[清穿]岳月
- 大唐:父亲您不造反,我造反!扑街蜘蛛呀
- 团宠小奶包我是全皇朝最横的崽抹茶红豆
- 年代重生:从拒绝倒插门开始腊肉角豆煲仔饭
- 考上清北后,黑道老爹气进ICU微尘尘尘尘尘尘
- 修罗君王夜行月
- 开局十个神话天赋,你怎么和我打锦衣少年
- 不灭钢之魂奇迹型MKIII
- 太祖奶奶她修仙月晓惜
- 签到系统砸中我,带飞了我的国梦之萱
- 柯南之我不是蛇精病烟火酒颂
- 三国第一毒士,曹操劝我冷静一笔长生
- 转生女妖,与重生千金拯救世界宇宙鸽
- 余生漫长半步顾封
- 你好,路知南不是妖腻
- 清穿之种地日常迷途未返
- 不逢春酒猫儿
- 变成少爷的漂亮小可爱后,他摊牌了赤色轨
- 浪与礁石liy离
- 讨好失败河央
- 在男团磕队友cp,我社死了杏逐桃
- 渣了男主后我含泪做恨(1v1)斯人有疾
- 精灵宝冠(西幻,1V1)解冰
- 烟娘(1V1,高H,古言)倾清
- 穿书成恋爱脑霸总后moontage
- 在霸总梦境里逃生商御
- 我在古代当策划满座江南
- 旦那(父女 1v1)春与愁几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