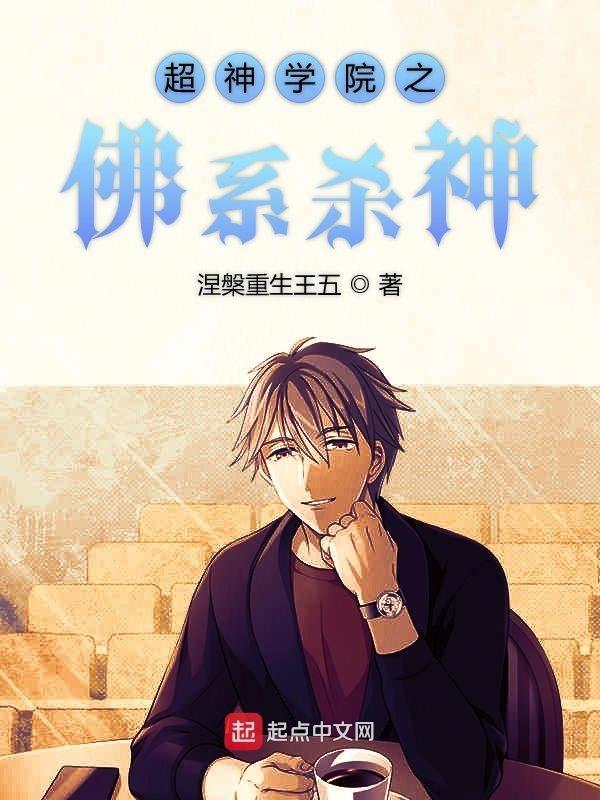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0章(第1页)
后来又用各种方式,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几部经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全弄到手看了。
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用飞一样的速度阅读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
现在完全不行了。
后来又把文革前那十几部著名小说读遍了。
记得从一个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糙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糙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
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
从糙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
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
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
但母亲看看我那副样子,宽容地叹息一声,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让我赶快出去弄点糙喂羊。
我飞快地蹿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时我真感到了幸福。
我的二哥也是个书迷,他比我大五岁,借书的路子比我要广得多,常能借到我借不到的书。
但这家伙不允许我看他借来的书。
他看书时,我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悄悄地溜到他的身后,先是远远地看,脖子伸得长长,像一只喝水的鹅,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靠了前。
他知道我溜到了他的身后,就故意地将书页翻得飞快,我一目十行地阅读才能勉强跟上趟。
他很快就会烦,合上书,一掌把我推到一边去。
但只要他打开书页,很快我就会凑上去。
他怕我趁他不在时偷看,总是把书藏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就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地下党员李玉和藏密电码一样。
但我比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高明得多,我总是能把我二哥费尽心机藏起来的书找到;找到后自然又是不顾一切,恨不得把书一口吞到肚子里去。
有一次他借到一本《破晓记》,藏到猪圈的棚子里。
我去找书时,头碰了马蜂窝,嗡的一声响,几十只马蜂蜇到脸上,奇痛难挨。
但顾不上痛,抓紧时间阅读,读着读着眼睛就睁不开了。
头肿得像柳斗,眼睛肿成了一条fèng。
我二哥一回来,看到我的模样,好像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先把书从我手里夺出来,拿到不知什么地方藏了,才回来管教我。
他一巴掌差点把我扇到猪圈里,然后说:活该!我恼恨与疼痛交加,呜呜地哭起来。
他想了一会儿,可能是怕母亲回来骂,便说:只要你说是自己上厕所时不小心碰了马蜂窝,我就让你把《破晓记》读完。
我非常愉快地同意了。
但到了第二天,我脑袋消了肿,去跟他要书时,他马上就不认账了。
我发誓今后借了书也决不给他看,但只要我借回了他没读过的书,他就使用暴力抢去先看。
有一次我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三家巷》,回家后一头钻到堆满麦秸糙的牛棚里,正看得入迷,他悄悄地摸进来,一把将书抢走,说:这书有毒,我先看看,帮你批判批判!他把我的《三家巷》揣进怀里跑走了。
我好恼怒!但追又追不上他,追上了也打不过他,只能在牛棚里跳着脚骂他。
几天后,他将《三家巷》扔给我,说:赶快还了去,这书流氓极了!我当然不会听他的。
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为书里那些小儿女的纯真爱情而痴迷陶醉。
旧广州的水汽市声扑面而来,在耳际鼻畔缭绕。
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
当我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趴在麦秸糙上低声抽泣起来。
- 开局签到送封号斗罗南方乞丐
- 我就是富二代!一块硬板床
- 无尽债务伯洛戈Andlao
- 东京电子游戏大亨小鸡啄小米
- 岳不群也要模拟人生8月12
- 君临法兰西孤山钓雪
- 全职之职业欧皇闪光哈士奇
- 我能修改人设词条堪梦01
- 一万个我纵横诸天正经沧月
- 从成为妖怪之主开始咸鱼配饭
- 神父马维柯学的菜头
- 修仙从熟练度面板开始无人能比的卡比
- 斗罗之我编造了未来视频符何君
- 诡异星巫白银黑铁
- 我的手机能挖矿卖艺小青年
- 我在古代当名师三羊泰来
- 诸天大明联盟饿祸
- 从武侠世界开始种道古今兮
- 黑龙国度不死长河
- 影帝他不想当太监江公子阿宝
- 大明:我,朱棣第四子星月长江
- 人在龙族,刚成魔法少女一叶封妖
- 足坛第一狂徒真狼魂
- 剑本是魔惰堕
- 从天才开始无敌于斗破a小白b
- 傲娇女神爱上我叫我红烧肉
- 见鬼曲小蛐
- 鱼目珠子崽崽猎手
- 病态痴迷(校园青梅竹马H)巧克熊
- 万人迷[穿书]风雪添酒
- 老赵老赵孙潇潇
- 音符瀑布
- 霸总雇我对付他命定的小白花女主启夫微安
- 没你就不行之新征途林木儿
- 孟大小姐惘若
- 四合院之闫家老大星际旅客
- 女儿拔掉了我氧气管东方燿
- 30条短视频助星球避开天灾睡觉能人
- 软腰河豚没有毒
- 欲望娃娃蜜丸
- 地窟逃生百倍奖励[无限流]尝寒
- 炙野八宝粥粥
- 末世被丧尸圈养(强制 nph)xoxoxo12
- 高武:开局觉醒武神系统一夜暴富啊啊啊
- 继父(,甜宠h)四重奏
- 宠头到尾(青梅竹马h)石矶娘娘
- 香江第一长嫂[八零]浣若君
- 龙魂特种兵东方小少
- 长央红刺北
- 文城余华 ="y">巧克熊
- 不会点兵,但我依然是大汉战神呆呆两脚兽
- 体王易尘
- 被关十万年,我疯了,也无敌了一条幺鸡
- 原体与崩坏末与未
- 辞掉996后,我成了荒星主爱做白日梦的小土豆
- 综影:一个穿越者的日常沉默的胖子
- 好好宠自己风雪心君
- 沙奈朵:养成天才少女当联盟冠军你怎么知道我是小猫
- 生常晨印
- 穿书后她只想苟鸡举张张
- 糊咖新赛道,专注玄学吓哭娱乐圈一三乙
- 我,天牢狱卒,靠着系统偷偷无敌花九枝
- 神豪:开局被美女系花邀请吃饭惊雨之后
- 第一召唤师喵喵大人
- 快穿:拯救炮灰女配进行时养养眼
- 洛克人ZERO传玛奇玛爱吃草莓
- HP隐藏救世主她来自斯莱特林白霖柳
- 姐姐别乱来,我真不是傻子了小楼听雨
- 神豪:我真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德亿双馨
- 官途:权力巅峰任风萧
- 为师教你们的都是真东西啊有钱必生女儿
- 楼兰儿女丑菊
- 玄幻:他背景通天燕纷飞
- 极道武学修改器南方的竹子
- 踢养子断亲情真少爷重生后不舔了十里良缘
- 牵错了红线搭对了绳蚁吼
- 在男团磕队友cp,我社死了杏逐桃
- 旦那(父女 1v1)春与愁几许
- 精灵宝冠(西幻,1V1)解冰
- 导演她怼遍娱乐圈古尘风
- 饮鸩止渴莫逢君
- 你好,路知南不是妖腻
- 余生漫长半步顾封
- 京西往事/今夜渡港宋昭
- 猫又都过去吧
- 热雨李诶诶
- 在霸总梦境里逃生商御
- 讨好失败河央
- 慎言别雀
- 帝王养蘑菇的注意事项丹青落
- 热雨李诶诶 O长官竟是天然撩若水